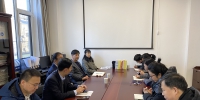李兰永:家庭化迁移体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
流动人口中最初流动的先行者逐步在目标城市稳态生活,其配偶、子女、老人仍然居留在农村,这部分人口在节庆或农忙时节在农村和城镇之间做“候鸟式”流动。这种“候鸟式”流动不仅造成了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三留守”问题,还使城镇化水平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如何破解“候鸟式”流动人口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解决“候鸟式”流动人口问题的诸多途径中,家庭化迁移体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是统筹解决“候鸟式”流动人口问题富有前景的选择。
“候鸟式”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内涵和外延
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候鸟式”流动人口,特指平时工作生活在城镇,节假日或农忙返乡,多数在户籍地有家庭留守成员的农民工,它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部分。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口迁移是指户籍登记地的永久性改变。而事实上,存在大量非户籍登记地或居住地非永久性的改变,这种情况常常被称为人口流动。家庭化迁移是指一种有别于原子化个体迁移的新的迁移形态,在农民工个体迁移的基础上,携带眷属到城镇工作或生活,最终实现以户籍迁移为标志的家庭整体迁移。
“候鸟式”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候鸟式”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是促进我国城镇化由“半城市化”向“完全城市化”转移的最佳选择。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以家庭为单位组织人口迁移,与个体迁移相比,减少了人口向农村回流的可能性,降低了人口迁移的风险。“候鸟式”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理念。人口的“候鸟式”流动给农村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家庭化迁移能有效解决“三留守”问题。“候鸟式”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转型。“候鸟式”流动人口不再直接经营土地,长期以来找人代为耕种和转包,埋下了土地规模经营的种子。家庭化迁移将简化农村土地利益关系,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候鸟式”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历史、现状、问题与趋势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候鸟式”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历史,城乡比较收益驱使农村劳动力以原子化形式向城镇转移,伴随着农地经营的便利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逐步扩大,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整体迁移。分析“候鸟式”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现状,农村土地转包和农业机械化发展,使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规模快速扩大,家庭化迁移按照单身-夫妻-子女-老人的次序进行,流动人口城镇社会融合程度加深。当前影响“候鸟式”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主要问题包括,“候鸟式”流动人口就业和住所的合法稳定性仍然受到一定挑战,而合法稳定就业和住所(含租赁)是户籍迁移的基本条件;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从操作层面没有完全获取城镇居民待遇,流动人口老人养老目前找不到突破口;尽管已建立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制度,但是流动人口参保仍然存在一些操作层面的壁垒。为破解这些问题,家庭化迁移应明确各类型城市家庭化迁移的基本情况和演化趋势,优选出向某类型城市家庭化迁移的路径。
“候鸟式”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策略选择及对策建议
家庭化迁移应立足就近城市群。特大城市人口聚集态势还在加强,但是特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不是家庭化迁移的首选目标。依托户籍地附近的城市群,根据不同家庭条件迁移到城市群各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才是最佳选择。建立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候鸟式”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陆续迁移到城镇,需要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项公共服务,政府应根据常住人口数量抓紧建立公共服务成本分担机制,保证“候鸟式”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均等享受公共服务。化解人口回流农村的潜在风险。保持“候鸟式”流动人口城镇就业或自我雇佣的收益稳定,才能使其在城镇生存和发展,因此应建立“候鸟式”流动人口培训体系,提高其就业和自我发展能力,规避大规模回流农村的潜在风险。一旦出现回流,应在坚持农地经营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积极为回流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并提供稳定的住所。建立“候鸟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促进机制。整合“候鸟式”流动人口农地收益权、宅基地处置权,剥离其农地经营权,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模式。引导在城镇有合法稳定收入和住所(含租赁)且具有市民化特征的流动人口,在自愿的基础上有偿向村居集体交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三权”,然后将所享受的农村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决策参与权整体转移到城镇社区,最终实现户籍迁移。妥善处理“候鸟式”流动人口与农村的非经济关系。“候鸟式”流动人口与农村除了经济利益关联之外,还有乡情乡谊的联系,这在本代人看来难以割舍,政府应出台政策尽力维护城乡之间的文化关联。但是乡土文化牵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将随着“候鸟式”流动人口的代际转换而逐渐淡化。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