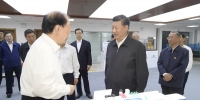传统文化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曾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2000多年之久的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俱进的;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的原则。
我体会,上面三点说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我想对此做一些阐释,供朋友们参考。
不同学派的“相反而相成”
春秋(前770至前476年)战国(前475至前221年)这500年左右,是中国古代历史发生剧变的时期,从血缘宗法社会向统一的传统社会的发展时期。当时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诸子学”,有阴阳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兵家、杂家、小说家。各个学派的思想相互争辩,又相互借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东汉时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同的思想学派“相反而相成”。
举一例来看:春秋战国时期,道家主张“天而不人”,要人们向大自然回归。儒家荀子批评这个主张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儒家认为,仁义道德是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道家批评说,儒家这个观点狂妄无知。庄子举例说,毛嫱、西施是人见人爱的美女,但鸟类看了都会高飞而去,鱼儿见了会沉溺水底,可见人的审美标准不能为鸟类鱼类认同;又如人喜欢住在华美的屋子里,泥鳅却要生活在污泥里,而猿猴却喜欢栖身于树林中,可见人们居住需求不能为动物界认同。如此类推,怎么能说仁义道德是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呢?
可见道家和儒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儒家也看到道家在“天道”探索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认识到在知人时不可不知天,因而也从理论上努力为儒家学说提出自己的“天道”依据;在这方面,子思、孟子取得了很大成就。而道家在批评儒家夸大“人”的作用的同时,也意识到儒家的理论成就,在战国中晚期,道家的后学、即秦汉之际的道家,就试图调和道家自然天道观与儒家道德教化的矛盾,吸取儒家关于人的认识学说的某些成果,如《吕氏春秋》一书就体现了融汇儒、道思想的特色。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相反而相成”,有了长远的生命力。
讲到这里,有必要介绍孔子“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春秋时期,“和”与“同”的区分是很清楚的。晏子曾对齐景公说,“和”就像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高低、长短、徐疾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组成一首完整和谐的乐曲。
孔子丰富了“和”与“同”的概念。他的论点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说,君子以“和”为准则,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独立思考,加以判断。
“和”不是争,而是在相互影响中使事物得到发展。“百家争鸣”是“和而不同”的具体表现,包含有百家相助相长的内容。
现举一例。中国古代出现了完整的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见于《礼记·礼运篇》,这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的著作,其中关于“大同”社会有一段具体的描述:
“大同”社会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准绳,不同于“天下为家”的社会。
在“大同”社会中,社会财富不是私人所藏有的,而是为大家所共同享有的。
在“大同”社会中,人人都要为全体利益而劳动。
在“大同”社会中,育幼、养老都有很好的安排,能劳动的人从事劳动,而失去劳动条件的人,由集体供养(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在“大同”社会中,大家相爱,没有权谋欺诈和盗贼掠夺,和平地生活而没有战争(“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在“大同”社会中,公共事务由大家来办理,在分工上可以选出人们信赖的人担任必要的工作(“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礼记·礼运篇》还说,在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时期,并非“大同”,乃是“小康”时代,由小康才能进入大同。
这样的“大同”理想,不但继承了早期儒家思想,而且在不少地方也继承了墨家思想,例如“选贤举能”和“尚贤”原则相似;“老有所终”一段又相似于《墨子·兼爱》中的一节,甚至“大同”这一名称也可能从墨家所说“尚同”沿袭而来。同时,《礼记·礼运篇》有些地方也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如称“大同”世界为“大道之行”,而“大道”则是道家的术语。可以说,“大同”理想主要源于儒家,同时也吸取了墨家和道家的某些思想,而非一家之专利,是“和而不同”文化观的体现。正因为有这种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生生不息,连绵不断。
儒学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学说
儒学和中国历史上其他思想学说都是与时俱进的,也有些学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未能传承下来,如墨家。还有的已融合于其他思想,如阴阳家。这里我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为例来做具体的阐释。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期鲁国昌平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他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学或儒家。何谓“儒”?商代,“儒”是对主持祭祀人员的称谓。春秋时期,儒成为以传统礼仪知识谋生的人。孔子是一位学问渊博、道德高尚的儒。他精通“六艺”即诗、书、礼、乐、射(射箭)、御(驾车)。又研究整理了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献:《诗》《书》《礼》《乐》《周易》和《春秋》。后因《乐经》佚失,称为《五经》。
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西周以来的旧礼制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对此孔子在感情上并不认同,但是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办起了“私学”,主张“有教无类”:不论是贵族或平民,也不论出身何处,都可以到他的私学来学习。由此可见,孔子选定了一条路,就是用教育和文化去改造社会的道路。
孔子逝世后,弟子门人将其言论加以整理、订正,编纂成书称为《论语》,它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经典。在思想上,孔子有三个重要的理念,即:1.“道”:人生目标、理想,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君子忧道不忧贫”等;2.“仁”,即爱人,由亲亲扩展到爱大众,进一步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孔子的核心理念。3.礼与乐,孔子认为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石。
西汉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将孔子列为“世家”,对孔子身世做了详细记载,写了赞语:“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至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还写了孔子弟子们的列传。
战国时儒学分为八派,其中有两派影响最大:一是子思、孟子学派;一是荀子学派。
孟子主张治国者应实行“仁政”,具体说,就是农民要有一定的财产权,征税要有限度,使农民生活改善。倡导“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孟子还从哲学理论的高度论述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与生俱来的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经过后天的学习,将这些人性中的潜质加以发扬,形成君子必须具有的仁、义、礼、智四性。在孟子看来,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操行,即道德自觉,而其他动物没有。孟子还提出“大丈夫”的概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君子身处富贵温柔之乡,不能丧失志向,身处贫贱困苦之地,不能改变人格;身处强暴威胁之时,不能丢掉气节,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这些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宝贵财富。战国末年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吸收法家的若干思想,主张德治与法治二者相结合,这影响了后来中国封建社会中治国理政的思想。
当中国历史演进到汉武帝时期,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武帝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在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力求使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以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我们从中国历史中看到:儒学真正形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逐步实现的,并非一蹴而就。历史情况是这样: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鼓励读书人深入研究儒家经学。经学是解释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在经学建立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五经》用汉代和汉代以前的文字写成,有所不同,于是有了经今古文之争,士大夫各自引经据典,争论不休。还有,当时在汉代流行的一些神学迷信也影响了人们对《五经》的理解。再有,解释儒家的经书,从其中要提炼出怎样的理念?以上的问题不解决,很难使儒学真正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东汉章帝时才得到解决。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京师洛阳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儒家经学的会议,皇帝亲自裁决,统一对经书的理解,规定对经书的阐述都必须贯穿“三纲五常”的核心理念。所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要指出的是,孔子没有讲过谁为纲的问题,他只是说做君的要像做君的样子,为父的要像父的样子,为人子要像儿子那样。但“三纲”并非为此,它反映封建宗法制度的特质,三纲的君臣关系是政治关系,父子、夫妻是血缘关系,师长、朋友从属于政治关系和血缘关系。三纲说对封建宗法制度来说确实抓住了最基本的原则,以君权和父权来稳定统治秩序,这种人身依附的关系体现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本质特征。三纲适合于中国的传统封建制社会,不适用于今天。
从中国历史可以看到,由于封建社会的需要,西汉时有“五经”,东汉时“五经”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唐朝为“九经”,宋代为“十三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权统治以经学为武器,而民间也以经学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家规家教等都同经学有关,反映出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天下的状况。
到唐代,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对儒家经书的解释不统一,命大臣撰《五经正义》。这部书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因为时势不同,自东汉初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佛教与儒学的关系成为统治阶层和文人学士共同关心的大问题。还有,东汉初形成的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在唐代也有很大影响。在唐代不可能再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局面。
中华文化善于研究、改造、吸收外来文化,并非简单的排斥。唐代统治阶层中有人相信佛教和道教。许多文人学士坚守儒学主旨,但认为应吸收佛、道中的某些理论观点,以充实儒学。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从理论方面看,大体是三个方面:1.佛教中某些宗派关于人的主体意识“心”的论述,影响了儒学;2.佛教中某些宗派对“本体”理念的阐述对思想家们有很大影响;3.佛教对“高深智慧”的重视也影响了儒学。中国儒学平实易行,只谈人的生命、生活,不谈生前死后,在理论思维上需要提升,将印度佛教改造成为中国佛教,也就是佛教儒学化。这方面的文化思想体现在宋、明理学中。宋、明理学在本体论、心性论,在哲学思想方面比早期儒学有了很大进展。至于道教关于人长生不死的论述,其中有大量迷信,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理论思维,这些也需要有所分析,有所取舍,使儒学更加充实。正如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在一首诗里所写:“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儒学有活水源头,与时俱进,故儒学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从唐代开始,到北宋时形成理学,南宋时理学体系进一步完整,“三教合一”真正定型。所谓“三教合一”,佛教、道教是宗教,而儒学并非宗教,是一种有效的教化,“以文载道,以文化人”。
“经世致用”的丰富内涵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经世致用”指高尚的情操、境界,一种博大的胸怀。
“经世致用”把国家和民族与个人联系在一起,表现为民族气节和操守;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反对压迫、掠夺和侵扰,这是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的标志。
西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格”观念,与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如董仲舒倡导“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强调“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放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观点。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19年受尽折磨而不改其志,始终坚持民族气节,留名青史。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往往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对此我们应进行具体分析,不可由此而否定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
中国思想文化史告诉我们:做人和做学问这二者应当统一,而前者比后者更加重要。将学问用在匡时济世上,首先要有高尚的人品,要有气节和操守,特别在国家民族的大节上,不允许有污点。如果做不到,所谓“经世致用”就失去了灵魂。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不只是一种方法,而是信念、理想、大道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
还有,“经世致用”又表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宋代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年)所写《岳阳楼记》名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此文中,他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官者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个人的感情?他回答说:在朝廷做官,要情系百姓,不在朝廷也要有对于国家的忧患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种情怀的文字表述。
“经世致用”也是不畏强暴的求实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在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的时代,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有比较充分的表现。他们将“经世致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里我想以黄宗羲(1610—1695年)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为例略作说明。他说,夏、商、周三代,“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是“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人)客(人)颠倒,君主将天下视为己有,独占天下之利。君主没有取得天下以前,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去追求一己之私利。得到天下以后,又不惜“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由此,黄宗羲得出的结论是:“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是他的反对君主专制制度(针对明朝末年的状况)的言论,是当时经世致用精神的表现。
黄宗羲经世致用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工商业的重视,具有“富民”思想。他反对奢侈浪费、沉迷享乐的社会习俗,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使百姓“去凶一循于礼”,凡是对民无用而有害者,一概去除。
总之,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经世致用不只是端正学风的要求,而是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对于真理的追求精神。
当然,经世致用也是我国历史长期积累的端正学风的文字表述。
《论语·学而》第一句话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习”有两个含义,一是温习,一是践行。在孔子看来,学生们躬行实践,将所学到的理论用于实际行动,十分必要。总之,儒学倡导“行胜于言”。
战国末期的荀子认为行是知的来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强调知来源于行,行高于知,学问的目的在践行。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年)解释什么是“行”,他说:行就是“以身心尝试”,指人的有目的的行为,含有试验的含义。
还要提到清初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年),他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有许多时间在长途跋涉中度过,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三个月以上。朋友们赠送了两骡两马,用以驮负所需书籍笔墨。旅费靠友人接济,间或做些小买卖。一年有大半时间在旅店中度过。他边调查边记录,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名著。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包含有学者的人品、视野、学风、精神诸多方面的融汇和结合,内涵丰富深刻。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只谈两点,供大家参考。
首先,中华传统文化中包括深刻的哲学理论思维,其中的变易之学(或“有对”之学)成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于事物“有对”和变化的思想,在《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老子》)、《墨子》、《易大传》中有深刻的论述。
《道德经》提出美丑、难易、长短、高下、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攻守、进退、动静等,认为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道德经》讲两个方面“相生”、“相成”、“相形”、“相倾”、“相和”、“相随”等。引申开来,在思想文化上,要有所继承,也有不取,践行“贵柔守雌”。《易大传》与此不同,主张刚强为主,柔弱为副。
《孙子兵法》发展了老子的“有对”思想。老子“有对”思想的弱点在于把变化看作是无条件的,因而人们对事物发展的前景无法预测。《孙子兵法》比《道德经》深刻的地方在于它指出了转化的条件,在各种条件中,人是最重要的,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一定的高度。
先秦时期的“变易”之学:“有对”之学,到宋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又有很大的提升,比如,北宋时关中学者张载(1020—1077年)在其著作中,说明事物运动,“动非自外”、“动必有机”(内因)。他举例说,“人一身中两手为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复有长短,直至于毛发之类亦无有一相似”,正是这种“不齐”,才使得“两端”发生相吸而又相斥的关系,于是才有人类的繁衍、社会的进步。同时张载也指出,相互排斥的“两端”并非永远对立,“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变易之学(“有对”之学)最后归结到人自身,这就是《周易》中所说“自强不息”。这里要提到,近代学者梁启超于1911年到清华演讲,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后来成为清华的校训。
其次,中华传统文化一贯重视历史记载,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汗牛充栋。其中古代史学特别关注社会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含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记载。司马迁作《史记》,其礼、乐、律、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全面记载了汉武帝以前的典章制度。班固撰《汉书》,改书为“志”,成律历、礼乐、刑法、食货、祭祀、天文、地理、沟洫、艺文十志。唐代还出现了专门的制度史专著,如刘知幾的儿子刘秩著《政典》,杜佑撰《通典》。总之,中国古代史书记载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近似于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因而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的成就都有文字记载,便于世代相传。
还要提到,中国古代教育保证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夏朝距今四千多年,那时已出现了学校。西周时学校制度初具规模,包含国学和乡学两个系统,春秋时演变为官学与私学。春秋末期孔子办私学,打破西周官学的入学等级性,实行面对社会的开放教育。这样文化的传承就有了宽广的渠道。
唐末五代时期的书院,经北宋时期初步发展和南宋时的突飞猛进,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应天书院等。这些书院由名师主持,师生之间探讨学术,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朋友们,我讲的太长了,在结束演讲时,我想说:我们要加强文化自信,必须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化多下功夫学习、思考,把优秀的成果消化吸收,成为我们的精神根基。
作者:张岂之,出生于1927年,江苏南通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及学术领导经验,主持过一些重大科研项目。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