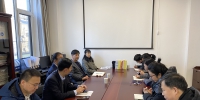颜景高:论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功能
有观点认为,“普世价值”超越于国家、民族和宗教之上,并不涉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而是亟待中国全面吸收并且全盘借鉴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从历史起源上说,“普世价值”却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特有的核心价值观,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而“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因而它的意识形态功能毋容置疑;从社会本质上讲,“普世价值”虽然在“形式上”具备了普世性,却无法超越资本文明自身的历史限度,因而并不能正确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当下实践。事实上,唯有超越“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窠臼,做好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从而创造性的开启世界文明形态更替的方向。因此,深入把握新时期意识形态的本质,进而把握“普世价值”的历史意义和缺憾,从而切实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弘扬,是当前理论界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一、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功能
从理论起源上说,“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表征着近代启蒙理论所达到的哲学认识论高度,正如J.巴林所指认,“对于托拉西来说,意识形态是哲学上的基础科学。”作为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托拉西开创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因而无论从《哲学大辞典》到《外国哲学大辞典》,还是从《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到《英汉哲学术语词典》,都明确表明“意识形态”概念源自于托拉西的“Ideologie”。从词义学上来解释,法文的Ideologie可以理解为中文的“观念学”,事实上,作为观念学的意识形态在托拉西那里有着明确的含义,即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可靠性”。根据托拉西的理解,任何观念都源自于人的感觉,也就是说,无法还原为人的直接感觉的观念必定是谬误的,因而意识形态的任务就是对形形色色的各种观念的“还原和辩误”,正是在此意义上,汉斯·巴尔特评论道:托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变成了社会的理论基础。”
从实践功能上讲,“意识形态”概念传播着近代启蒙精神,催生着宗教批判和制度嬗变的革命性力量,正如汉斯·巴尔特所指出:“在18世纪,宗教批判是国家批判的先导。”以托拉西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家们信奉的是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批判的是天主教的神秘观念,反对的是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根据意识形态理论所确立的原则,“意识形态的唯一任务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种种观念的还原。”由于宗教意识和“君权神授”理论都无法还原到人们的直接感觉,这些观念都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因而必须拒斥这些谬误观念所维护的国家制度,正是“托拉西的直接与拿破仑重建宗教的意向相冲突的反宗教观点”,导致法国意识形态家们与“封建帝制”的维护者们彻底决裂。历史的讽刺和幽默是,由于策动对外侵略战争打击欧洲其他国家的封建势力,拿破仑同时成为其他国家意识形态家们的真正救星,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指出:“如果拿破仑和他的法国军队未曾迅速地战胜我们,那些留在德国的自由之友会遭到更大的不幸。拿破仑确实从未料到自己会成为意识形态的救星。没有拿破仑,我们的哲学家和他们的观念一起会被绞刑架和车裂消灭的一干二净。”
因而从本质上讲,“意识形态家们”认识世界的终究目的是改变世界,正如阿尔都塞所认定,“作为再现体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或者说认识的职能)。”吊诡的是,以反对谬误观念为根本宗旨的意识形态概念从一开始就步入了“误区”,因为意识形态概念所依赖的感觉主义传统自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正如海德格尔所认定,“哲学总是不断地为误解层层包围,而这些误解现在大多又为像我们这样的哲学教授们所加剧。”事实上,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历程清晰表明,单凭人的感觉无法引伸出正确的认识论,更无法为所有的社会科学提供可靠的认识论基础,这种局限性正如马克思所评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意识形态还必然受制于特定社会环境的约束,因而关于意识形态概念“众说纷纭”的历史命运是注定的,特别是在“利益支配着我们的一切判断”的历史时代。
作为提供社会科学认识论基础的一种学科,意识形态理论的舆论导向总是关联着“意识形态家们”的阶级立场,更涉及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正如亨利希·马克思所认定:“要是哪一个研究过拿破仑的历史以及他对‘意识形态’( Ideologie)这一荒谬之辞的理解,那他就会心安理得地为拿破仑的垮台和普鲁士的胜利而欢呼。”从建构性的纬度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提供科学认识论基础的社会理论,它清晰表明了某种社会形态存在的非法性,并且系统论证了另一种社会形态存在的合理性,从而成为改造或者摧毁这个社会而采取行动的理论根据,正是在此意义上,葛兰西将意识形态上升为“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建构性意义鲜明的体现在文明形态更替的社会变革期,诸如代表着历史进步意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宗教迷信和封建特权的批判,以及代表着更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至上和资本垄断的批判。
从消极性的纬度说,意识形态往往反映着特定阶级对现存世界及其秩序的价值判断,从而衍变为主流社会思想观念的论证体系,最终蜕变为统治集团的政治话语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事实上,代表历史进步趋势的意识形态在取得思想统治地位之后,往往走向“意识形态的反面”,特别是进入社会形态停滞不前的“僵化时代”, 这鲜明的体现为意识形态要不被主流思潮“终结”了,要不就嬗变为“虚假”的社会思潮。一方面,社会主流思潮往往宣传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认定自己的时代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终极形态,如弗兰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中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就是意识形态发展的终极方向,正是在此意义上,丹尼尔·贝尔推导出“意识形态已经寿终正寝了”结论。另一方面,社会主流思潮往往宣称所谓的“普世价值论”,虚假的认定所属“特殊阶级”的利益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二、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核心价值观
新世纪以来的意识形态争鸣看似弱化了,意识形态形象也似乎淡化了,但毋容置疑,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受意识形态”操控的时代,正如阿勒文·托夫勒所指认,“新的意识加倍冒出来,它们分别以一个个对现实的梦想煽动追随者。”意识形态的“无处不在”首先鲜明的体现在其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无形渗透:作为论证当代人类社会存在状况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蕴含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形成了精巧而有效的机制,已经衍变为一种“物化”的社会关系,正如路易·阿尔都塞所概括:“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AIE),其属下有宗教、教育、法律、政治、工会、传播、文化等各种部门。”其次,作为表达当代人类精神生产活动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已经渗入人的无意识层面,并且内化为人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方式,即“他们不知道它,但是他们在做它。”其一,当前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泛指性的存在,它貌似不在但又无所不在,因为意识形态可以“指称任何事物,从曲解对社会现实依赖性沉思的态度到行动取向的一整套信念,从个体赖以维持其与社会结构之关系的不可缺少的媒介,到使得主导政治权力合法化的错误观念,几乎无所不包。”其二,当前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弥散性的社会存在,它貌似不在却又无时不在,因为意识形态正巧在“我们试图拜托它的时候突然冒出来,而在人们认定它会存在的地方反倒不会出现。”概言之,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意识形态的载体时而是概念,时而是形象,悄然进入人类的无意识层面,进而编织为一种 “合理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
作为当前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价值观念不仅表明一个阶级、政党和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更关涉到一个民族的根本道路问题,正如西方价值哲学的奠基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所指出:“一个民族若没有能力先行评价价值,就不可能存在;一个民族要自我保存,就不能依傍邻族评价的价值。”毋须庸言,意识形态仅仅用一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来塑造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想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融入到群众的血脉,进而内化为情感认同,外化为自觉行动,必须提炼并整合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作为社会的价值之魂,核心价值观既通俗易懂又凝魂聚气,将自身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发挥地淋漓尽致。一方面,朗朗上口、妇孺皆知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常识化”的意识形态,它促成了人们的价值共识,并且将其凝聚在以核心价值观为圆心的同心圆之内,在潜移默化中取得了人们在情感中的认同,诚如弗洛伊德所认定,处于同一圆中的人们“不过是一个装满了意识形态液体的容器,变成了外观上相同的一把裁纸刀。”另一方面,简洁明快、形象鲜明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通俗化”的意识形态,它促成了人们的观念认同,打通了意识形态与大众意识嫁接的甬道,并且有效弥合了利益冲突而导致的社会分化。
核心价值观引导着一定社会的主流民意和舆论氛围,培育着一个国家的道义基础和形象,从而决定性的开启了制度变革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因为“核心价值观可以简要的概括为‘制度精神’,它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制度、一个国家运作模式赖以立足、借以扩展、得以延续的灵魂,因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核。”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新时期的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渗透力日益彰显,影响力日趋常态化,这集中体现在:其一,新时期的核心价值观集理性化和感性化于一体,注重发挥社会舆论宣教功能,正如卡尔-穆尔扎所指认,现代社会中的“政权的机制不仅是强迫,而且是说服,以取得被领导者的积极配合。”其二,新时期的核心价值观集理想性和现实性于一体,充分发挥社会利益导向,正如侯惠勤先生所指出:“纯物质利益扩大到思想政治利益,从单纯个人利益扩大到家庭、民族、国家,也就是说,把利益的‘个人计算和‘社会计算’结合起来。”其三,新时期的核心价值观集社会性和集体性于一体,聚焦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熏陶,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的情感认同,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认定,“家庭熏陶重在怡情。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核心价值观得以传播的源泉。”
核心价值观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多层次融入,足以汇聚起一个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足以支撑起一个国家富强的伟大梦想,哪怕执政党在某个时期犯了错误、走了弯路,正是在此意义上,塞缪尔·亨廷顿强调:“有的社会当生存受到严重挑战时,也能推迟其衰亡,遏制其解体,办法就是重新振作公民身份和国家特性意识,振奋国家的目标感,以及国民的文化价值观。”毋须庸言,如果一个国家背离核心价值观进行所谓的改革,那么带来的只能是动荡不安、甚至是国家解体、民族灭亡,譬如前苏联的例子,“随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改革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推进,以‘多元化’来反马克思主义;用‘民主化’来反社会主义;倡导‘自由化’引向资本主义”,前苏联解体了!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社会意识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三、普世价值的时代意义和缺憾
从概念界定的层面上讲,“普世价值”的内涵并不是确定无疑的,诸如国内外学术界的争鸣、媒体界的争论、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议等等,百度百科将其概述为:“普世价值”是英文“universal value”的意译,其实译为“普适价值”更为准确。普适价值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出于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之价值观念。”遵循这种界定,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 法治 、人权等等都可以囊括在“普世价值”的范围之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社会不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时代。从功能定位的纬度上来界定,“普世价值”是指一种社会形态核心价值观的“自大”,或者说它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简约化”后的“自恋”,比如封建社会形态自诩的“三纲五常”,又如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或者以其它形式“改头换面”出现的所谓“普世价值”。
毋容置疑,资本主义社会的“普世价值”发挥过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资产阶级的进步观念“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从建构性功能的层面上说,18世纪的《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提出了“天赋人权”的理论,从理论层面上论证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主张,正如皮埃尔·勒鲁所指认,“法国革命把政治归结为这三个神圣的词:自由、平等、博爱。我们先辈的这个格言不仅写在我们的纪念性建筑物、钱币和旗帜上,而且铭刻在他们的心中。”正是秉承“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观,资本主义性质的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宗教神权的专制特权思想,进而导致这些宗教观念所维护的封建主义制度轰然倒塌。从消极性效果的层面上分析,虽然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引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随后此起彼伏的“工人起义”清晰表明,“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仅仅是资产阶级特殊利益集体的遮羞布,或者说是资本社会劳资矛盾的漂亮舞衣,进一步说,普世价值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虚假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指认,“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而在市场交换领域之外,当广大工人阶级“威胁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安全,就立即取缔,把‘自由、平等、博爱’代之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
事实上,遵循“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分析,“普世价值”的内涵和功能在当代已经有了显著的新变化,这集中的体现在“自由、民主、人权”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观替代,正如李慎明先生所明确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当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理论,是对自由资本时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作为文明社会形态核心价值,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以及人权等思想观念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最美丽的花朵,至今仍指引着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但也毋须讳言,“自由、民主、人权”发展成为西方普世价值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奴隶制、种族歧视以及性别歧视等等,正如张维明先生所考证,“‘自由、民主、人权’的推广普及过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觉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经过长期英勇的抗争,并和西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渐把这些本属于世界上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价值观,其内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动过程中被大大丰富了。”
吊诡的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逐步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推行“霸权主义”的舆论工具,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承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从客观层面上讲,世界一体化的飞速狂飙源自于资本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因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主观层面上讲,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源自于帝国主义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秩序的宣传需要。从本质层面上讲,普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肆宣扬或者强行输送源自于垄断资本逐利的本性,因为“资本有了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便活跃起来,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冒绞首的危险。”正是在此意义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不遗余力的策动“颜色革命”、“和平演变”乃至“局部战争”, 拉美危机、苏东剧变以及海湾战争的惨痛教训清晰表明,普世价值的“渗透或者干涉”引发的“政变”给输入国送来的不是梦寐以求的 “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巧强豪夺”以及国内生活状况的“惨痛不堪”。
四、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弘扬
“普世价值”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渗透有着鲜明的政治意图,它依托学术讨论和网络宣传,攻击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正如秦晓先生所明言,“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士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反对的,是根据这些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依托全球化的资本载体和话语霸权,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国际舆论不遗余力美化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且不遗余力地攻击“势力范围之外”的意识形态,丹尼尔·贝尔因而直言不讳地断言:“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倡导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导创造出来的。”正是在这种国际舆论背景下,美国政府几乎每年都擅自发布“中国的人权报告“,横加指责中国的“西藏问题”、“民主问题”以及“人权问题”;美国的公众人物,还动辄在国际媒体上抹黑中国形象,妄言中国的“专制体制”、“权威政府”、“非民主国家”等等。
马克思明确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地表现了各个社会阶级的斗争。”国际政治格局发展史清晰表明,国际垄断资本势力输送普世价值的目的,并不像某些“人权斗士”所希望的那样,给我们带来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而是妄图分裂社会主义中国并从中渔利,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当前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和理论自觉,充分揭露国际垄断资本的实质和图谋,进而旗帜鲜明的抵制“普世价值观”的肆意渗透。一方面,我们要深刻把握“普世价值”的虚假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了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从本质上讲,普世价值所代表的无疑是有资产者、特别是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另一方面,我们要清醒认识“普世价值”渗透的恶果,戈尔巴乔夫奉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进行改革,后果却是国内外垄断资本的盛宴、人民群众的苦难,正像马克思所指出,“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内在一致,都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凝结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旗帜鲜明的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进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事实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功能,必须进一步做好核心价值观的“语言凝练”工作,以期更贴近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特别要注意的是,核心价值观的“语言凝练”必须奠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上,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客观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进一步讲,核心价值观还必须做好“语言简化”工作,以期形成通俗易懂的、简洁精练的、朗朗上口的群众语言,从而内化为人民的认同、外化为群众的行动,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认定,“观念要转化为行动,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简化观念;第二,提出一个真理的主张;第三,把两者结合起来付之行动。”
遵循语言凝练和语言简化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必须做到与人类文明同进步、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根源、与科学社会主义同命运。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进一步凝练并简化为“平等、公正、仁爱”,在这个犹如“缝鞋子”的价值序列构建中,平等为“底”,公正为“帮”,仁爱为“线”。首先,平等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性观念,正如皮埃尔·勒鲁所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除了平等的信条外,再也没有别的基础。”无论是中国佛教倡导的“终生平等”,还是基督教倡导的“人人平等”,无不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程中对“平等”的现实诉求。其次,公正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观念,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始终不渝的价值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虽然影响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但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第三,仁爱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辅助性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深入挖掘和阐释其讲仁爱、重民生,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中国的仁爱思想和西方的博爱思想交相辉映,提升着当代人的认识水平和道德境界,仍然是我们应该珍重并且发扬广大的思想遗产。
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要坚持固本培元、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的总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大致而言,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让人民在实践中感知 “平等、公正、仁爱”的社会导向功能,在观念中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身的不同层次和社会定位,从而使平等、公正、仁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达到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程度”。具体而言,要切实发挥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功能,用具体的法律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真正让“平等、公正、仁爱”观念融入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而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政策支撑、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制度惩罚。
(作者系山东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