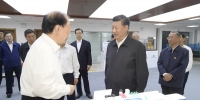光明日报:面向世界的儒学——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前瞻
由国家文化部与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The 7th Session of the World Confucian Conference)将于2015年9月27日至29日,在山东省曲阜举行。届时,在这个国际化的儒学研究与交流的高端平台上,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位儒学专家学者,围绕“儒家思想与当代价值建构”这一主题,开展交流与对话。
为了开好这次盛会,以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重要讲话和关于山东工作重要批示精神,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组委会于近日邀请部分知名学者,就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所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研讨。本刊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儒学价值观的和平导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宋志明
宗教价值观通常着眼于人性中的阴暗面,立足于外在性,即从人性之外、从神那里寻求人超越自我的外在根据。儒学价值观则不然。儒学着眼于人性中的光明面,立足于内在性,从人性中寻求自我超越的内在根据。儒学这种超凡入圣的价值取向,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来说,不失为一种宝贵资源。
儒学的这一思想方向发端于孔子,他把人性中的光明面称为“仁”。他强调,“仁”乃是人的内在品格,乃是人生价值的源头。按照这种思路,价值实现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理性选择:“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人在修己成仁时,表现出一种主动性,而无须受什么外在神秘力量的规束。
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孟子预设了一种价值理想,强调人应该善。至于实然人性,既有善,也有恶;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如果现实的人肯接受儒学价值理念,便可以使阴暗面得以抑制,使光明面得以发扬,通过修身的途径实现自我完善化。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向善的能力,叫作“良能”;生来就具有求善的意识,叫作“良知”。良知良能乃万善之源,由此而形成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由四端而形成四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即仁、义、礼、智。孟子的结论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我固有之”的意思,不是说人一生下来就是善的,只是说接受道德观念的前提,内在于应然人性之中。人性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之所在。
儒学大力倡导与人为善精神,为实施道德教化、造就礼仪之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儒学的淑世主义导向中,包含着尊重他人、尊重民意、与人为善、利群利他、忧国忧民、严于律己、推己及人、向往高尚人格等意向,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事实证明,儒学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念,提供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甚至可以说倘若没有儒学,中华民族不可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儒学把淑世主义导向应用于国际关系方面,便形成和平主义导向。在这一点上,儒学为中华民族培养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提供了良性培养基础。儒学讲究包容性,拒斥排他性,主张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主张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儒学从修身讲起,推己及人,进而讲到齐家和治国,最后指向“平天下”。儒学发端于中原地区,其创始人为汉族人,但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都认同儒学。儒学是中国各个兄弟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儒学只以自身的理论魅力吸引受众,决不借用外力、暴力向受众灌输。在儒学传向东亚的历史上,从未发生“一手拿经书,一手拿利剑”的情形。儒学“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理念是东亚各国和睦共处的精神基础。儒学这种和平主义的取向,在历史上曾成为东亚各国的共识,在当今时代则可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罗素赞许中华民族是“骄傲得不愿意打仗的民族”,对儒学的维护和平意向表示充分的肯定。
第二次启蒙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牟钟鉴
近代西方第一次启蒙运动摆脱了神学,解放了自我,抬高了理性,因而促进了科学与民主,推动了世界现代化事业。同时,信仰和道德被贬抑,资本释放了贪欲,自我成为新的上帝,理性成为双刃剑,人沦落为金钱、权力、野心的奴隶。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而利益集团仍然迷恋弱肉强食和斗争哲学,世界很不太平,面临诸多危险。因此有识之士提出人类需要进行第二次启蒙运动,摆脱自我中心主义,超越工具理性而构建道德理性,树立互爱互尊、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以便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常态。如果说第一次启蒙运动是理性的启蒙,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第二次启蒙运动应是道德的启蒙,口号应是“尊重他者”。当代美国比较哲学家安乐哲指出:个人主义价值观使人类选择错误信仰,失去道德和精神,走向自己的反面;人类必须实现对第一次启蒙的突围,走向以人为中心的信仰、道德与精神生活的第二次启蒙。于是作为新启蒙重要资粮的孔子儒学在沉寂了百余年之后开始在世界舞台上登场了。
从国内的形势看,国际上刚刚启动的新启蒙运动恰好与中国一场新的文化运动起步相衔接,真是机缘巧合。古老的中国在进入现代之初出现的五四运动,是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它是在救亡与启蒙双重合奏中进行的。它引进西方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成果如科学、民主、人权、法治,又引进社会主义,促使中国开始摆脱宗法等级和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并赢得独立和解放。但这次新文化运动受文化激进主义的制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儒学)”,因而带来过度否定中华文化传统、丢失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和道德精神的弊病,文化路向走偏了。“文化大革命”是反传统的极端化,它造成的灾难使人们觉悟到切断民族文化血脉的虚无主义的严重危害。于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国学的振兴,开始了中国现代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次运动是在民族文化自信自觉的过程中发生的,它的口号是“创新儒学”。它要使中华优秀文化在回归中国故土的同时走向世界。虽然事情刚刚起步,前程尚任重而道远,但重要的是社会风气已经发生转向,中华文化已在重生,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和改变了。
在山东曲阜举办的世界儒学大会已历六届,取得很大成功,产生广泛国际影响。它的特点在于:从孔子家乡的圣城曲阜向全世界发出儒学的声音,展示孔子的气象和儒学的精华。各国人士受到孔子人格的感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圣城,讨论儒学的当代价值,进行不同文明的对话,证明孔子是伟大的圣哲,当代中国需要他,当代世界也需要他。这次世界儒学大会以“儒家思想与当代价值建构”为主题,尤其突出社会道德。道德建设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形成各界各地各业道德先行的君子群体。为此,我为大会写了《重铸君子人格,推动移风易俗》的发言,试图运用孔子儒家君子论的丰富思想,重构当代新君子理论,提出“君子六有”论: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
“六经”的价值伦理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刘梦溪
对儒学未来的展望,取决于如何正确地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我们需要弄清楚与儒家学说相关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儒家的包容性,实际上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义涵。“六艺”后称“六经”。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
马一浮所说的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熊十力所说的立国做人的基本依据,高在何处?所据者何?一言以蔽之,曰“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梳理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永恒的价值理念,也可以说它们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道德理性精神。《庄子·天下》篇写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虽该篇之作者不知谁何,其对“六经”义理宗趣的阐释,不失为得义之言。
儒学的三个阶段
中国孔子研究院研究员 杨朝明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儒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即通常所谓“原始儒学阶段”,这是儒学创立与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孔子儒家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强调“正名”,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二是秦汉以来以至近代,这是“帝制中国时代”,是儒学走向民间,与社会密切结合的时期,可称之为“儒学发展阶段”。与先秦不同,这时期政治上皇权至上,适应专制政治的需要,逐渐强化君权、父权和夫权,儒学慢慢蜕变,染上了显著的“威权色彩”,呈现出为后世所诟病的“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近代以来,尤其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儒学进入第三个时期,可称为“儒学反思阶段”。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变动,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帝制时代,孔子被尊崇到极高地位,儒学是统治学说,新文化运动的矛头自然直指孔子,借以打倒儒学和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动,其思维方式上存在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但客观上却主要指向具有“威权色彩”的儒学,把被扭曲了的儒学主张看得更清。
对中国儒学进行这样的划分,有助于对儒学价值的认识。作为思想文化,孔子儒学的影响之大可以说罕有匹敌,而对其价值认识的分歧之大竟然也无与伦比。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在中国不断遭受外敌欺凌,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期,希望中华民族走出低谷,关注民族命运的人都思考文化问题,强烈“保守”传统的人多看到了原始儒学的真精神,而对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持“激进”立场的人,则更多地看到了作为“专制政治灵魂”的那个“偶像的权威”。难怪“新启蒙运动时期”有学者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们确实应该关注原始儒学,分清“真孔子”和“假孔子”,澄清误解,明辨是非,正确对待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随着学术事业的进步,人们对儒学的变化看得更清楚了。正如有的西方人士所看到的,因为有了孔子的学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时间虽然过去了两千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却仍然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那些价值观念。
从儒学自身的发展看,“反思”与“反省”仍然在进行。总体观察当下人们对于孔子儒学的理解,还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不言而喻,研究儒学如果不能把握“精髓”,就有可能竞相树旗立帜,标新立异,往往各执己见;推广儒学如果不能抓住“要领”,就有可能舍本逐末,事倍功半,乃至南辕北辙。“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儒学怎能发挥经世化民的作用。只要走近孔子那颗伟大的心灵,认真借鉴先圣先贤的智慧,就能看清通向大同世界的理想之路。只有深入走近儒学的世界,世界儒学的天地才能更加澄净。
儒家文化的可公度性
北京大学教授 王中江
自从晚清东西文化和传统大规模接触之后,中国的思想家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探寻两者中的差异性与普遍性,其中也有外国朋友加入到这一行列,如罗素。他虽然称不上是中国学问和问题的专家,但作为旁观者,他在《中国问题》中对中国文化中的普遍价值的认识,也领略到了中国文化的诱人之处和魅力。
儒家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用孟子的话说是“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但儒家从来就不否认文化中的普遍性。这可以从两大方面说,一是儒家认识到了文化的普遍性和差异性、文化的多元性和共识的关系。《周易·系辞传下》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宋明道学家说的“理一分殊”。这种思维肯定了有“我们”,肯定了我们有“共同的世界”,同时也肯定了“他者”,肯定了有他者的“不同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按《礼记·中庸》的说法,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儒家传统和资源如何对当代的中国人和世界作出贡献,依赖于我们对它的深度观察和视点。在儒家思想和学说中,它有一些内在的普遍性。其中之一,是它的仁爱精神。若尊重他人的愿望是一个普遍性的价值,那么儒家的“仁爱”精神就具有这样的内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好就体现了这一方面。仁爱本质上是普遍同情,它主张包容一切、关照一切。儒家始终把“反求诸己”和“不尤人”作为修身的中心,同样是尊重他人。儒家的“天人合一”和“万物一体”思想,有机主义和整体主义世界观,教导人类还要学会同万物相处,善待作为自然的他者。儒家“仁爱”中的孝亲层面,主要是指明了一个人实践仁爱的出发点和入手处,并不是把它狭隘为只是孝亲。
再如,儒家始终把人的尊严和价值放在人的道德自觉和人格境界上,从不以出身和身份来衡量人的优越性。儒家的人性论,主要是人性平等论,它为所有的人都赋予了共同的人性。人与圣人的差别只在于学与不学的问题。儒家没有印度的种姓意识,也没有古希腊的奴隶观念。儒家的“礼”虽然注重区分人类事务中的“差异性”,其许多礼仪规定了“差别待遇”,但不能说这是主张等级制和人类的不平等,在现代社会的许多礼仪活动中,人们所受到的礼遇不是也很不一样吗?
总而言之,儒家的学说和思想,总体上倾向于普遍性和可公度性思维,而主要不是特殊性和差异性思维。《吕氏春秋·有始》的一段话可以代表儒家的这种思维:“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众耳目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众异。〔众异〕则万物备也。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
不同的文化和传统既是自身的、自我的,但同时又是开放的、包容的和彼此可以分享的。在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文化并存的前提下,我们更需要以理性和真诚展开交往和深层的对话。
世界儒学大会的世界性
山东大学教授 王学典
世界儒学大会,要和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进行对话,比如说儒学和自由主义对话。你只有和主流对话,你本人才能取得世界的影响。如果只是和边缘对话,那么你的成果也是边缘的。像安乐哲先生,杜维明先生,包括贝淡宁先生,他们都是从自由主义阵营杀出来的,而且他们都看到了自由主义的缺陷。我们应该通过对话,展现儒学的价值,彰显儒学弥补这个缺陷的可能性。关键是我们怎么设置好的命题,好的话题,然后使我们这个影响能够吸引在世界上更多的人来参与,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关起门来搞儒学不行,我们是世界儒学大会,我们必须把在思想界,在理论界,在前沿有影响力有号召力的人请到大会上来。
儒学如何在实践上复兴是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儒学复兴不能在研究院,不能在讲堂上,不能在会议上。儒学复兴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按照儒家的原则来创造一种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有关儒学的命运,儒学的复兴。山东大学曾经提出一个建议叫曲阜文化特区。由此我想,我们不妨拿出一个地方来,按照儒家的原则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创造一个新的社区。我们在历史上不是没有这种先例,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就是唐代。唐代的生活方式于当时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各国使遣唐使都到中国来。至今我们从日本和韩国都能看到唐代的影子。今天,在自由主义已经占世界主流地位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更高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要吸取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更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汲取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精华,综合创造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儒家的思想与理念的确是奠基在伦常日用当中的。如果不能恢复这一点,我们研究得再多也不行,只和自由主义对话也不行。我们还要在生活上在实践上怎么创造一个新的生活样态,一个新的生活典范,这个更有吸引力。如果我们这个典范创造出来,那么在其他生活方式下感觉不舒服的人就可以到中国来。这里更有人情味,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父慈子孝这一套都能得到兼顾。我们对此要有信心,同时还要有一个规划设计。让儒学不仅和乡村结合,而且和城市相结合,我觉得这样才能期待儒学的振兴。
儒家智慧与世界难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周桂钿
世界之大,问题很多,难题也很多。人类不断地用智慧解决这些难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类解决这类问题的智慧,称为科学。二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类处理这类问题的智慧,称为人文,或叫文化。以文化人,用文明转化人们的思想,化解人际矛盾,使之达到和谐。
西方人从自然界中弱肉强食现象体会出优胜劣汰道理,努力探险,深入研究,大大提高对自然界的认识,发展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提高了人类在自然界的影响力。接着,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人将其他种族的人也当作客观的征服对象,形成了流行于全世界的殖民地现象。有人为英国殖民政策唱赞歌。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美国应该感谢英国的殖民统治,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独立运动,应该受到谴责。英国殖民统治好,还是华盛顿独立运动好?没有历史观念的人对于如此简单的事实都分不清是否。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单极独霸于世,开始以世界警察自居。几位美国总统都公然宣称“美国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换言之,符合美国利益的就是真理,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就是谬误。这还有什么道义可言!美军入侵伊拉克一周年的时候,美国总统高兴地说:“终于让世界人民看到美国的力量!”这等于说,入侵伊拉克是为了显示美国的力量。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大儒孟子说:要以德服人,不要以力服人。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孔子也曾说:“远人不服,修德以来之。”两千年之后,缺乏文明的霸主还沾沾自喜于以力服人!“远人不服,出兵以压服之”,这就是霸权的逻辑。压服总是压而不服,力不足以抵抗,就要想出各种办法来报复。这些办法,有的是正常的,有的是不正常的,有的是恐怖主义。霸权主义走向极端物极必反,不会道义,必将走向灭亡。中国古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儒家重视和,将和作为出发点,也作为奋斗的目标。讲和就要强调德,如果没有德就无法实现和。但是只讲德也不行,不用实力战胜邪恶,也实现不了和。孔子讲“为政以德”,他又非常赞扬管仲、子产这些法家先驱的政治改革。孟子讲“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董仲舒提出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些都是德法并用的思想,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由于德法并用的合理性,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包容性,形成民族复杂、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这些丰富的政治智慧,解决了许多社会难题,也将为解决世界难题贡献智慧。
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存山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相“因”继承和“损益”发展有着自觉的意识。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里的“因”可以说就是文化连续性发展的“常道”,而“损益”就是对原有的文化有所减损和增益,以实现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新命”。
虽然孔子讲了夏、商、周三代之礼(文化)有相“因”的继承性,但他并没有说出此相“因”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认为,儒家文化真正的“常道”应是先秦儒家与秦后儒家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以此为判据,如果从“祖述尧舜”讲起,那么,崇尚道德、以民为本、和谐社会,可以说就是儒家文化所承自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代之王的“常道”。而孔子把“仁”提升到道德的最高范畴,因此,儒家文化的“常道”又是以仁爱精神为统率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24日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我认为,这里说的“固有的根本”“自己的精神命脉”,当就是指中国文化的“常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一种发展创新,但它“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即中国文化发展“变中有常”的辩证法。
习近平特别强调:“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渊源。”我认为,这里说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可以说是对儒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之“常道”的一个精辟概括和表述。“常道”之常新,就在于它不仅传承久远,而且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渊源”,这正是我们要传承和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常”或“因”是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而“变”或“损益”就是要实现文化发展的“新命”。那么,在中国的古今之间有哪些重要的变化呢?第一,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已经转变为以工商为主的市场经济;第二,从君主制已经转变为民主共和制;第三,从服务于君主制的科举制已经转变为服务于社会多种需要的现代教育制度;第四,从经学的“权威真理”的思维方式已经转变为广义的“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
儒家文化要实现现代化的“新命”,一方面要适应这四个方面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要转化或优化这四个方面所出现的问题。如市场经济中的义利关系问题,政治制度方面的以德治国与自由、民主、法治的问题,教育制度方面的人文素质(“明体”)与工具性知识(“达用”)的问题,思想观念方面的继承经学之“常道”与“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王国维语)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是需要现代儒学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来解决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年在曲阜市召开的“世界儒学大会”承担着重要的学术使命。